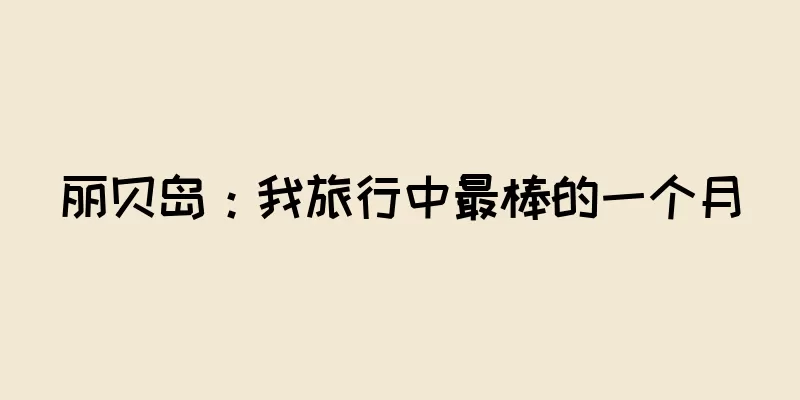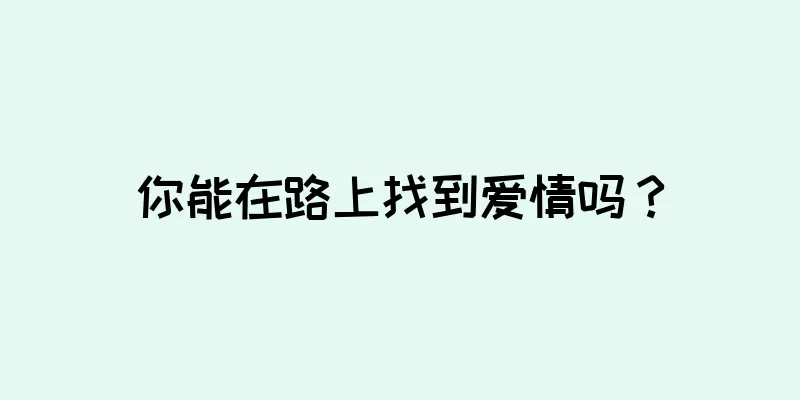2006 年 11 月,我原本计划为期一年的环球旅行已经进行了 5 个月。当我给父母发邮件告诉他们我还好时,我看到收件箱里有一条消息:
“马特,我被困在丽贝岛。我不能按计划来见你,但你应该来这里。这里是天堂!我已经来这里一个星期了。在日落海滩找我。——奥利维亚”
我的 MySpace 好友奥利维亚 (Olivia) 约好在甲米 (Krabi) 和我见面,那里是以石灰岩喀斯特地貌、攀岩和皮划艇闻名的旅游胜地。
我在地图上查找了丽贝岛。我的旅游指南上只提到了一点点。那里真的很偏僻,需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到达。
当我环顾拥挤的网吧和繁忙的街道时,很明显皮皮岛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热带岛屿天堂。人群又回来了,海滩上满是死去的珊瑚,船只似乎环绕着岛屿,水被一层薄薄的……好吧,我不想知道。一个更安静、更平静的天堂很有吸引力。
“我两天后就到,”我回答道。“只要告诉我你住哪儿就行。”
两天后,我乘渡轮前往大陆,然后乘坐长途巴士前往港口城市帕克巴拉,再乘渡轮前往丽贝岛。当我们经过荒无人烟、丛林密布的岛屿时,我漫步到顶层甲板,看到一个男人正在为前往丽贝岛的少数人弹吉他。
他讲完后,我们开始交谈。
保罗身材高大,肌肉发达,身材瘦削,剃着光头,留着少许胡茬。他的女友简也同样身材高大,体格健壮,有着棕红色的卷发和海蓝色的眼睛。他们都是英国人,一直在亚洲游荡,直到他们准备搬到新西兰,他们计划在那里工作、买房,最终结婚。
当我们在阳光下休息时,我问道:“你们住哪儿?”
“我们在岛的最远端找到了一个度假村。据说那里很便宜。你呢?”
“不确定。我本该和我的朋友住在一起,但我还没有收到回复。我没有地方住。”
渡轮靠近岛屿后停了下来。丽贝岛上没有码头。几年前,一位开发商试图建造一个码头,但由于当地渔民(他们以少量费用将乘客送上岛)的抗议,该项目被取消,开发商也神秘失踪了。
当我登上一艘长尾船时,我把我的人字拖掉进了海里。
看着它们沉下去,我大叫道:“妈的!这是我唯一的一双了!希望我能在岛上弄到一双。”
保罗、简和我去了他们住的酒店,帕特也加入了我们,他是一个爱尔兰老人,同样没有地方住。酒店俯瞰着一个小礁石和小小的日出海滩,那里将成为我们在岛上逗留期间的主要聚会场所。
我决定和帕特同住,因为我还没有收到我朋友奥利维亚的消息,而且分房更划算。那时省下几百泰铢就意味着路上多花一天或少花一天。保罗和简住在一间可以俯瞰大海的平房里。(他们的露台是我们这个小团体最受欢迎的聚会场所之一。)
我们出发去找我的朋友,她说可以在日落海滩的 Monkey Bar 找到她。
当我们走到岛的另一边时,我发现奥利维亚说得对:丽贝岛就是天堂。这里有美丽的丛林、荒芜的海滩、温暖清澈的蓝色海水和友好的当地人。晚上只有几个小时有电,酒店和游客很少,街道都是简单的土路。丽贝岛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。
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奥利维亚。日落海滩并不大,Monkey Bar 是海滩上唯一的酒吧,它是一家茅草屋,里面有一个放冷饮的冰箱和几把椅子。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,然后点了啤酒,问了一些典型的旅行者问题,然后就坐在那里闲聊。
帕特打呼噜,所以住了两晚后,我搬到了岛中心的一间平房,每晚 100 泰铢(3 美元)。这间硬木小屋坐落在一家供应当地最美味鱿鱼的餐厅后面,漆成红色,屋顶为白色,门廊很小,内部几乎空无一物——一张床、一台风扇和一顶蚊帐——似乎是这家人为迎接从未到来的旅游浪潮而建的。
我放弃寻找新的人字拖了。没有一双我喜欢或合脚的。我会等到大陆,然后光着脚走路。
我们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核心小组,随着其他游客的到来和离开,这个小组不断壮大和缩小。除了戴夫(一个年轻的法国人)和萨姆(一个饱经风霜的英国侨民,十年来每个季节都来岛上居住,有一次在最后一艘船离开后被困在那里),我们是岛上唯一的西方常驻居民。
我们每天都在玩西洋双陆棋、看书和游泳。我们轮流去不同的海滩,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保罗和简家附近的海滩上闲逛。游泳距离内有一块小岩石,悬崖峭壁,非常适合浮潜。我们偶尔会离开丽贝岛,去探索附近国家公园的荒岛,钓鱼和潜水。没有什么比拥有一整座热带岛屿更美妙的了。
晚上,我们会轮流去餐厅吃饭:我住的旅馆老板的餐厅,Mama's 餐厅供应新鲜鱿鱼和辣咖喱,Castaway on Sunset Beach 供应马萨曼咖喱,Coco 餐厅供应其他美食。之后,我们会去 Monkey Bar 玩沙滩游戏、喝啤酒、偶尔去酒吧喝酒,还会玩西洋双陆棋。当发电机关闭时,我们会在睡觉前打着手电筒喝酒。
日子似乎永无止境地过去。我原定的三天行程就这样过去了。我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。
“我明天就走”成了我的口头禅。我没有理由离开。我身处天堂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保罗、简和我成为了好朋友。我们在小组内组成了一个小团体。
“你们到了新西兰打算做什么?”我问。
“我们会在那里工作几年,建立自己的生活。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回到英国,”保罗说。
“我这次旅行要去那里,所以我会去看看。这是我回家路上的最后一站,”我回答道。
“你可以和我们在一起。无论我们在哪里,”简一边说,一边把大麻烟卷递给我。
有一天坐在海滩上,我有了一个想法。
“你知道什么会很酷吗?一家环保旅馆。新西兰会是一个完美的地方。拥有一家旅馆不是很酷吗?”
“是的,那会很有趣,”保罗说。
“我们可以称它为温室,”简回答道。
“这是一个很棒的名字。”
“是的,说真的。”
保罗说:“我敢打赌我们一定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。生态友好型场所风靡一时,而且那里空间很大。我们将拥有花园、太阳能电池板和所有其他设施。”
我们半认真地考虑我们的旅馆,每天都在讨论细节:旅馆会是什么样子,我们如何获得资金,床位数量是多少。这只是一个白日梦——但这样的梦想帮助我们在海滩上度过了美好的时光。
有一天,妈妈家的账单突然翻倍了,我们才再次意识到时间。
“这是怎么回事?这条鱼昨天才半价啊!”
“现在是圣诞节!每年这个时候欧洲人比较多,所以我们就提高了价格。”
啊哈,资本主义处于最佳状态。
圣诞节还有另外一层含义:我很快就要离开了。
我的签证有效期只到新年前,所以我必须先去续签,然后才能去帕岸岛度假。
我不想离开。
我们仿佛置身于天堂。保罗、简、帕特和奥利维亚都留下来了,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从家人身边撕裂了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们。
但签证迫使我这么做。
保罗、简和我决定一起过圣诞节。这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们穿上最干净的衬衫,漫步到 Coco's 餐厅享用豪华西式晚餐。
“我给你们买了一份礼物。”
我递给简一条几天前我看到她盯着的项链,并递给保罗一枚他很羡慕的戒指。
“哇哦。太棒了,伙计!谢谢!”保罗说道。
“不过这很有趣,”他继续说道。“我们也给你带来了一些东西。”
那是一条手工雕刻的项链,上面有一个毛利鱼钩。这是他们对于旅行者的象征。后来我戴了好几年,它象征着我们的友谊、我在岛上的时光以及我的身份。
旅行使友谊的纽带更加紧密。当你在路上时,过去已不复存在。你或你遇到的任何人身上都没有家里的行李。只有现在的你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享受当下。没有要参加的会议、要办的差事、要付的账单或责任。
我曾听说,一对夫妻每天平均在一起度过四个小时。如果这是真的,那么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相当于四个月,但感觉就像是四个月的三倍,因为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忘记“现在”。
我再也没有回到丽贝岛。这里蓬勃发展的开发项目会打破我心中的完美形象。我看过水泥街道、大型度假村和人群的照片。我无法忍受看到这些。丽贝岛是我的海滩。完美的旅行者社区。我希望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。
几年后,我在新西兰再次遇见了保罗和简,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团队的其他成员。他们在外面的世界做着自己的事情。然而在那一个月里,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
当我收拾好行李,一个月来第一次穿上鞋子时,我向 Plick Bear 告别了,那是我在门廊上发现的破烂泰迪熊,后来成了我们的吉祥物,我希望未来的旅程会和我即将离开的旅程一样美好。